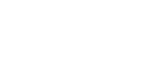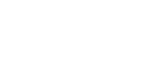安定区域的形成和定西城区的变迁
| 招商动态 |2016-10-21
“新莽权衡”的出土地巉口,是交通要塞的咽喉地带,曾盛极一时,历史上在“丝绸之路”的开通及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今天,由于巉口所处的特殊地理交通位置,又新一轮引起了广泛关注。巉口又是征战杀伐兵家必争之地,定西市安定区境内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战役,都发生在巉口及周边区域。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北宋大举伐夏。宋将李宪一路从临夏、临洮出兵,过马啣山,夺取兰州后,乘胜率兵东上,直至巉口。巉口以南到定西城区为定西北川,巉口以北为关川河上游谷地,再北便是青石峡,出峡就到会宁界马堡。李宪一不作,二不休,沿河进击。夏兵且战且退,倚青石峡之险要,阻击宋兵。宋兵锐不可挡,大败夏人于石峡之中。宋兵一路追打,出石峡,进至屈吴山(今靖远东部),攻打啰城川(讹为打拉池,今靖远共和),兵锋直指葫芦河(今宁夏境内清水河)。当时宋廷因两路兵溃败,便急令李宪旋师本路,安养士气,乃全师而还。此后,为防御西夏入侵,出于军事需要,11世纪末,自北而南筑会宁关(会宁界马堡)、平西寨、安西寨,定西寨、通西寨(陇西界通安驿)。至此以巉口(安西寨)为军事要塞,以定西为政治中心的四“西”才初具安定行政区域的雏形。
第二次,也是最著名的,公元14世纪六、七十年代,明将徐达与元将扩廓贴木儿(民间称王保保)之间的一次战役。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元)四月,大将军徐达会诸将于凤翔(今陕西凤翔),率师西进陇西,移师安定,并相继攻克会宁、静宁、平凉、庆阳,九月徐达自平凉凯旋还京。十二月王保保乘徐达还京之机,便又自张掖、酒泉率兵围兰州数月,终未能攻破,听说明军将至,只好解围而去。(1370年)四月,徐达率师10万到达安定,在今定西城北近五里处筑点将台(中山垒,俗称福台墩),王保保亦率兵10万东移,在定西县城北约五十五里处筑点将台(将台墩),形成南北对垒之势。东西两面,涧大沟深,两军各自择涧择沟,安营屯兵,一日叫战数次,胜负难分。元军使偷袭之计,亦末奏效。后来徐达动员全军,点将出战,亲临前线,官兵死战,奋力拼杀,大败元军于巉口地域及附近的乱坟滩(汉墓群)。王保保仅携妻、子数人,逃出青石峡,向北过黄河,直遁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至此,明军扫清了黄河以东甘肃境内的元部残余。此后,明军西征收复河西,实现了明朝对甘肃的统一。
西岩山下,一座大楼巍峨屹立,各色式样的小汽车来来往往,西装革履的男女进进出出。西岩山上,庙宇俨然,松柏森森,香烟袅袅,木鱼声声,不多些个世外人打理着一块香火之地。楼里人不注意山上人,山上人亦不关注楼里人。楼里人在上班下班、加衣减衣、月薪节假的交替中感受着时光如水、岁月如歌。山上人在日出日没、云舒云卷、花开花落里打发着时日,过着一年又一年。
山下是世间的繁衍地,山上是世外的修行处。举步之路,咫尺相望,默契相对,各行其是。到底什么是人生真谛?楼里人搞不清楚,山上人亦不大明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由于各自的际遇和社会的选择,便有贫富贵贱和不同的生活方式。
山下西河与东河交汇地带从一条街发展到今天初具规模的定西城区,自从有了西岩寺,山上人不看也得看,就象流行歌曲一样的道理,不是能拒绝得了的,脚下这块世俗地熙熙攘攘,由小变大。――
首先是宋朝,荜路蓝缕,披荆斩棘,修了南北走向的一条街,现在大城小学及敬东厂所处位置是当年的繁华之地。到了明朝,又向南面进行了拓展,现在永定路与南大街形成的大什字便成了这个城的中心。由原来的南北两个城门变为东西南北四个,且在城中有城楼和钟、鼓之楼,形制上成为古代当时中国较为完备的小县城池。本是一个很不规则的小县城,却被美称为头西尾东向北展翼的凤凰单展翅,并附会上了不着边际的凤凰来仪传说。
历史上,定西城区曾经出现的繁盛在明朝。据有关资料,在明中期,牌坊林立,殿堂雄伟。豪宅名园,华屋别墅,市肆栉比,盛极一时。说起在明朝的繁盛,不能不提到曾是明朝一品天官(最次也相当于现在的国务委员)、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人事部部长)的定西籍人张彩。尽管全国当时的繁盛也是大气候使然,但在定西城中的“张府”又为这个小县城增色不少。
张彩,进士及第,明史有传。虽然记述负面的多,最后不幸“剉尸于市”。但就像被逮住的贪腐高官一样,不是没有勤奋上进的成长过程和曾经的优良品行及出众的才华能力,想来也肯定有过自己勤勉努力的奋斗史和鹤立鸡群光彩耀人的一面。历史的云烟已散去500多年我们不去评说他的功过是非,由于他是安定人中职位做得最高的一位,只这一点,说起他尽管不值得炫耀,但也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光彩(有研究材料认为张有被冤枉的成分)。
作为历史人物,有必要追寻一下他在故乡的留痕。当然座落在敬东厂东南角的“张府”早已荡然无存,但只埋了一只靴子的衣冠冢在安定区东岳南阳一个被称为张家坟湾的地方,处在东山西麓的半山腰。那里山环水绕,林草丰茂,砖砌的正面朝西的牌门做工精细,古朴庄重,三个倒U形门洞,中间大两边小。牌门为明时所建,雕以花饰,撰刻额联。时间最重要,时间把一切变得不重要,曾经的显赫和不得善终的遭遇最后归于“荒冢一堆草没了”的常态。张家坟湾在安定区来说不失为一处不可多得的具有人文价值的山水景观。
定西城历经了明朝的辉煌和清朝的延续。说到清朝,有必要提一下县令许铁堂。许是地方文史界经常提及的一任父母官,因为清廉的名声和诗篇的流传而被颂扬。不是说创造了精神财富被人颂扬有什么不对,但是作为地方父母官的角色,除了清廉几乎再没有可恭维的地方。许是有些书生意气,书生意气难免有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像张慧在《渐台悲歌》中说的,你的愿望是良好的,但行得通吗?比如许提出赈灾,要求上面拨些款子,但未能实现,好心不能办好事。“坚白反见诬”,政治的东西不像书生想的应该不应该那样简单。可以说,许有写诗的才气和清廉的品质,但搞政治肯定不是他的强项。就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悲剧,尽管当时社会黑暗腐败,但被罢免贫困潦倒流落街头的县令大概不是太多吧!这到底是谁之过?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角度看,该如何评判“许铁堂现象”?
话又说回来,历史上在安定任过职的县令多的是,随便一个应该比许有政绩,就是政绩最大的一位,姓甚名谁,有谁知道,传颂下来了吗?这的确是个难以破解的悖论,为百姓造福的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几乎没有给地方百姓带来福祉但写了有些诗篇的许铁堂却成了世代传颂的对象。大概只有一种解释,曾经的悲欢场景都烟消云散,不见了踪影,“国家不幸诗人幸”,而文化是永恒的。
几百年兴败衰盛。到了1949年,由于多年战乱和民不聊生的背景,定西城已是满目疮痍,萧条无有生气。解放后,重心又移至新开拓的中华路,开始新一轮发展,习惯上称新市区。经过“文革”,所剩古建全部拆除,古城面貌全然无影。
2003年定西撤地设市、撤县设区,随着安定区委区府大楼在西岩山下的落成和西环路的开通,再加上市委市府办公楼设计在现城北的福台村,定西城迎来千载难逢的大规模扩建机遇。定西城区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经历了四次飞跃式的变动发展,范围和规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是“凤凰涅磐”,不知又要创造出什么美称来取代凤凰单展翅之说。
外地人惊叹定西城区的巨变,认为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城市。地方上“肉食者”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时代遵循社会规律的理念与老百姓的想法有了契合点。安定人思谋着把洋芋由土蛋蛋变成金蛋蛋,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由于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国家对城市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再加上招商引资效益的显著,一座座楼房像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真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不是我不明白,而是变的太快。
林立的高楼在阳光下烁烁发亮,大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市面上商铺接蹱繁荣昌盛,新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景观建设已初具规模。几十座塔吊同时做业,建筑工地热火朝天,定西城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手笔,高起点的拓建,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正象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最初的一条街,即现在友谊广场的位置,居然又成了今天定西城区的中心!离开原点回归原点,这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
法本无法世外人,变不离宗天下事。山寺牡丹争妍开,人间芳菲年又年。
 招商热线:400-151-2002
招商热线:400-151-2002